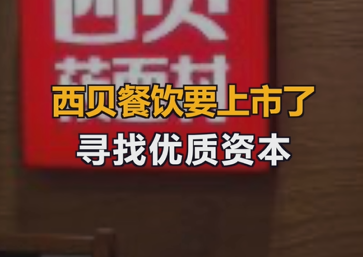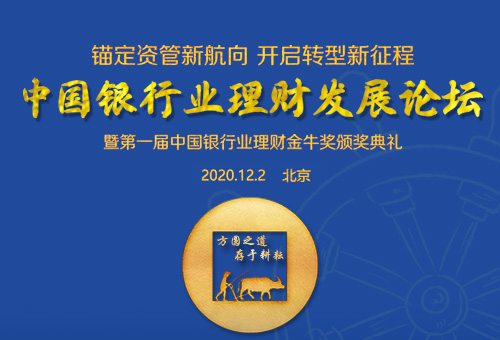數字經濟應促進社會福利最優化——讀《不安的變革:數字時代的市場競爭與大眾福利》
《不安的變革: 數字時代的市場競爭與大眾福利》 (德)阿希姆·瓦姆巴赫 漢斯·克里斯蒂安·穆勒 著 鐘曉睿等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10月 出版
數字經濟應促進社會福利最優化
——讀《不安的變革:數字時代的市場競爭與大眾福利》
⊙鄭渝川
德國反壟斷委員會主席、曼海姆歐洲經濟研究院院長、曼海姆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阿希姆·瓦姆巴赫,與德國《商報》記者漢斯·克里斯蒂安·穆勒合著的《不安的變革:數字時代的市場競爭與大眾福利》一書指出,基于數據運算和互聯網技術的數字經濟,而今已經深刻的改變了諸如歐洲、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提高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但數字經濟確實也挑戰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反壟斷監管準則,凸顯了隱私保護難題,并且還正在加劇社會貧富分化。
按照本書作者的觀點,數字經濟的發展目的,應當確立為促進社會福利的最優化,這又必然要保持數字經濟的充分競爭。
難題恰恰在于此。數字技術的應用帶來了一個顯著的悖論: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會推進競爭,提升效率,但越是新銳的技術,越有可能隨著競爭的加劇,最終導致贏家通吃的局面,削弱競爭甚至導致競爭消失。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數字產品和服務具有非排他性,邊際成本甚至為零,這意味著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是最有效的,沒能在規模之戰中勝出的企業,必然就被排除出整個市場。
數字經濟時代的顯著現象是,我們很難準確概括包括蘋果、亞馬遜、谷歌等企業的經營范圍,這些互聯網巨頭企業都是跨行業、跨市場經營的。數字經濟越來越突出地上演了平臺效應,企業搭建平臺,再通過持股、并購、自建等方式鎖定相關聯的、可以穩定帶來流量的服務領域,還可面向中小企業開放其他服務的互通接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沿用過去依照產品的市場份額判斷是否屬于壟斷的思路,就會變得無所適從。
傳統法律、監管思路,還會根據價格變化來判斷壟斷是否存在,因為壟斷者會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抬價。但這項標準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也失效了。互聯網巨頭企業名義上對消費者收取的費用為零,但是這些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三方甚至多方交易關系,消費者的數據和注意力成為了企業看重的資源。在目前,無論哪個國家和地區,還未能很好地根據互聯網巨頭企業的數據能力來建立區分壟斷的監管新規。
當然,從促進市場經濟、數字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科技創新的迭代速度大大超過了很多行業,使得數字壟斷現象往往難以長期持續。比如,20世紀90年代,曾被認為壟斷的雅虎搜索,很快被谷歌以及中國的百度在不同市場取代;微軟的IE瀏覽器曾被控壟斷,但很快,Chrome又成為新的領導者;臉書在美國市場獨大,卻也無法真正遏制TikTok的興起。這也為反對過早、過嚴實施數字壟斷制裁的論者提供了依據。
本書為此提出的建議是,從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出發,降低數據使用的壟斷。比如,監管部門可以設定規則,強化互聯互通,要求不同科技公司把自身收集的數據納入共享范疇,尤其是不得限定構成競爭的新創企業分享互聯網巨頭企業的數據。
社會市場經濟是二戰后,前聯邦德國提出的經濟發展思路,也就是彌補英美式自由放任經濟的缺陷,在不損害市場競爭活力的前提下,有效強化政府監管和再分配職責。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政策,遵循讓市場力量盡可能自由發揮作用的原則,重心傾向于讓發展成果為社會大眾所共享。作者認為,前聯邦德國在二戰后得以快速恢復,并于20世紀50至70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是由于社會市場經濟的模式為德國經濟帶來了較好的發展環境,而德國政府強化反壟斷,事實上也是讓德國中小企業長期得以保持增長活力的關鍵。
如前述,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反壟斷政策思路必須進行變化和調整。作者認為,監管部門應當意識到,今天經濟運行的方式、特征、規律都發生了變化,需要注意到壟斷代替競爭、數據代替價格、網絡自由職業者代替社會伙伴關系、分享代替產權等新趨勢,重新致力于建立與數字經濟兼容的社會市場經濟體系。
針對數字經濟總是難以避免從技術應用初期的過度競爭,發展到技術成熟階段的巨頭壟斷等問題,本書作者認為,監管部門要將反壟斷的重點轉向推動強制性的數據共享。不僅如此,如果市場在很長時間內沒有顯示出增加競爭的趨勢,政府就需要主動介入,制定新規則。比如,限制產品使用,鼓勵其他企業進入現由巨頭企業壟斷的業務領域,限制平臺企業接入其他企業的產品標準、方式等等。
而對于互聯網巨頭企業以及其他行業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經常出現的濫用用戶數據等做法,并因此使得用戶數據安全受到威脅等情況,作者表示,監管部門應切實保障用戶數據安全權益;檢查用戶獲得互聯網服務所必須接受開啟定位、錄音、通訊錄等權限的必要性;核查企業獲得用戶各項數據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用戶數據的方式;增加企業保障用戶數據安全的相關義務。
作者還在書中討論了“機器換人”的問題,總體持樂觀態度,即認為技術革命確實會帶來就業市場的劇變,但究竟會以什么樣的方式讓現有工作方式消失,并創造哪些新崗位,還有待觀察。更何況,新技術往往會創造許多與之互補的工作。
現在的問題是,數字革命還沒有使那些不斷消失的崗位,真正轉變成可以由零散方式外包,讓自由職業者承攬,并且收入和福利狀況得到保障的松散崗位。這意味著,即便在實現就業的人群中,貧富差距已經拉開。作者在書中建議,各國政府都應當根據數字革命的發展規律,強化教育培訓職能,推動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增強相應的就業技能。
此外,本書還談到了共享經濟等數字經濟所塑造的經濟新模式崛起對社會和產業帶來了影響。作者分析了出租車、房屋中介、金融業、通信服務、零售等不同行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出現的新變化,指出盡管數字革命總體上賦予了這些行業新的效能,但仍然會出現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比如,網上藥房興起后在德國等國家已經導致大量藥房倒閉,尤其是那些分布在偏遠地區、本就生意不好的藥房,這使居住在農村、郊區的民眾很難在心血管疾病突發時買到必備藥品。另外,要讓數字經濟創造的福利服務于全民而非寥寥幾個企業巨頭,就必須重視公平納稅的問題,通過健全法規以及跨國間協議來修補避稅、逃稅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