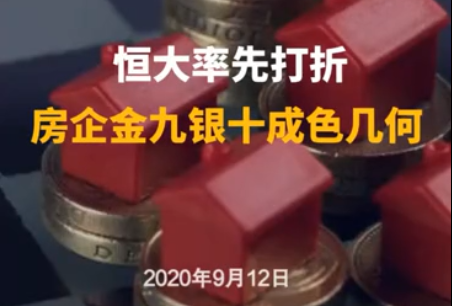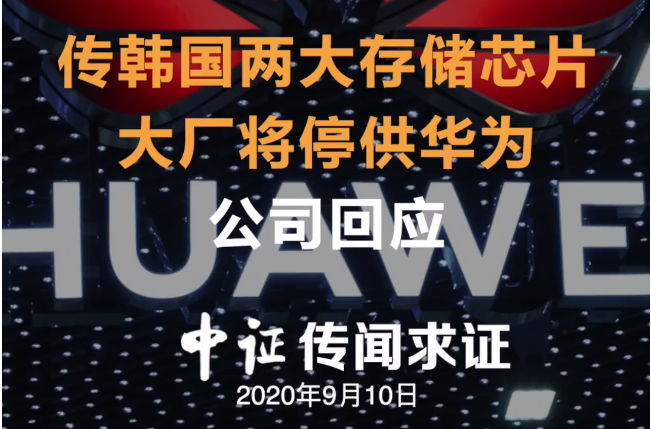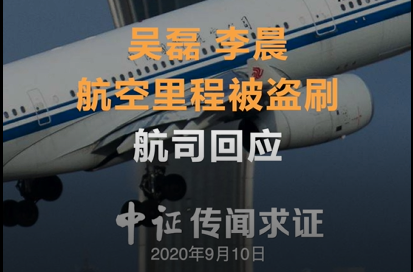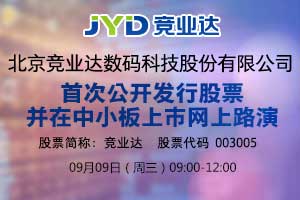興得了的產業 回得去的鄉村
70年前,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一書中探討了一個社會問題——“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他說:“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
70年后,當我們再次提出“鄉村振興”,村莊“空心化”嚴重,“留不住年輕人”依然是繞不開的問題。
“以前在家沒活干,不想待。想趁著年輕多出去走走看看。”談及離鄉的初衷,多數年輕人都會這么回答。
最近幾年,這種現象正在悄然發生變化。上證報記者近期在湖南、四川等地調研時,接觸到不少返鄉就業的年輕人。對于這些年輕人來說,能在家鄉有份穩定的工作和不錯的收入,就愿意留下。
就業和收入從何而來?鄉村振興靠什么?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回答了上述問題:產業興旺是重點。
春暖燕回巢
一年前,在外打工十幾年的隆忠奎回到了老家十八洞村。
“我女兒今年5歲,要開始上學了,我想回來陪她。”1989年出生的隆忠奎即將步入而立之年,和記者交流時這位苗家漢子憨厚的臉上帶著些羞澀與不安。
“小時候家里窮,父母都出去打工,我和弟弟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和父母感覺一點也不親。”談起回家工作的決定,他語氣中似乎多了些堅定,“我當年算是‘留守兒童’,不想女兒和我小時候一樣。”
“山溝兩岔窮疙瘩,每天紅薯苞谷粑。要想吃頓大米飯,除非生病有娃娃。”這曾是十八洞群眾貧窮窘迫生活的真實寫照。這個苗族聚居的山寨,隸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長期以來,十八洞人或以種幾畝田地為生,或外出務工度日,生產生活異常艱辛。
“我從17歲就開始在外打工,去過蘇州、溫州、寧波等好些地方,在外面待得都膩了,但回家又沒有工作。”隆忠奎說。
隆忠奎最終下定決心回家,還是因十八洞村發生的變化。2013年“精準扶貧”的思路在這里首次提出,十八洞村從此聲名鵲起,很多企業開始到村里進行產業幫扶。
湖南步步高集團就是最早進入的一家上市公司。2017年10月,步步高集團與十八洞村共同打造的十八洞村山泉水廠正式建成投產。這是當地第一個現代化產業項目。
9月初,上證報記者走訪了位于十八洞村大峽谷深處的山泉水廠。山巒林立,霧氣繚繞,山澗泉水氤氳著“遠看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的意境……
一棟碧綠色的廠房首先映入記者眼簾。走進廠房,十幾名工人正在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前忙碌著。來自十八洞村的山泉水經過水管輸送到這兒,經過十幾道設備,進行專業沉淀、過濾、消毒、殺菌等處理后,一瓶瓶帶著山里冰涼氣息的礦泉水就在這里下線。
回到十八洞村的隆忠奎成了水廠的員工,主要負責設備維修。“雖然沒有在外打工賺得多,但那種感覺很不一樣,回到家里睡覺都特別踏實。”
隆忠奎并不是返鄉的個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鄉村年輕人開始回歸。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目前各類返鄉下鄉人員已超700萬人,其中返鄉農民工比例超過68%。他們不但充實了勞動力,也帶回了開闊的視野、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
產業扶持要“量體裁衣”
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而產業扶貧是最長效的脫貧手段,也是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途徑。如何讓產業更“精準”地落地,這是政府和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開始,我們并沒有打算在十八洞村建水廠,之前考慮過臘肉廠、米酒廠,但是都達不到條件。”與記者說起建廠的經過,步步高集團董事長王填說,“后來我們發現十八洞村的山泉水水質特別好,最后才下定決心投資。”
這個被王填稱為“一號工程”的項目從構思到建成投產,只花了5個月時間。水廠給當地帶來的好處非常明顯。村里不但以“十八洞村”品牌入股,獲得15%的分紅權,水廠每年還與村集體保底分紅。2017年,山泉水產業分紅村集體收入50.18萬元,全村人均純收入達到10180元。
同樣是產業扶貧的“先鋒”,新希望集團也一直在四川大涼山進行摸索,從簡單的給錢給物向產業扶貧的方向轉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西昌公司總經理謝杰對此深有感觸。從1995年進入大涼山,到現在已經在當地工作了20多年,他說自己算得上是大半個涼山人。
“以前做扶貧項目,很多是送雞送豬,或者直接送錢。后來我們開始反思,送東西雖然是一份好心,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實際貧困狀況。脫貧還是要龍頭企業用產業去帶動,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謝杰說。
2016年,新希望集團開始實施“新希望1+1”精準扶貧計劃,先后在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等8個省份,依托自身產業特點,興建產業扶貧項目超過20個。截至2018年7月,累計已帶動建檔立卡戶實現脫貧668人,已簽約并帶動增收1679人,有望在2018年帶動超過3000人持續增收、穩定脫貧。
近年來,越來越多上市公司參與到產業扶貧的行列。滬深證券交易所近期統計了上市公司2017年扶貧工作的信息披露情況,據統計,兩市共有854家上市公司披露扶貧工作情況,開展產業扶貧項目超過4300個,投入約208億元,711萬名建檔立卡貧困戶受益,直接幫助超54萬人口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