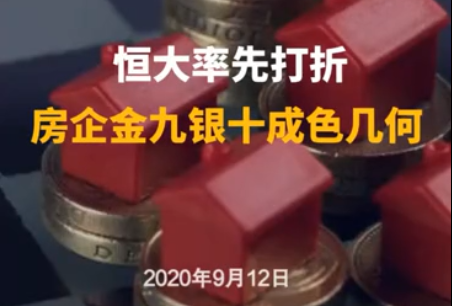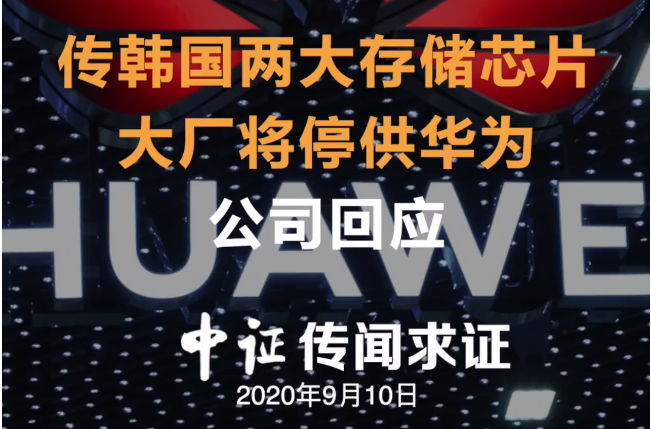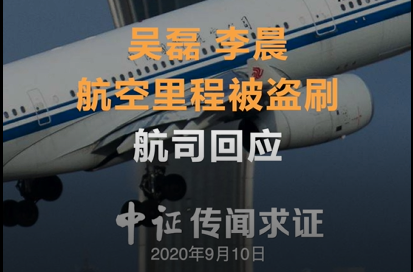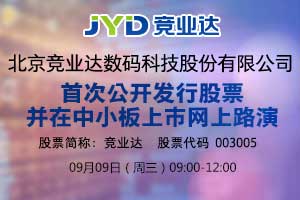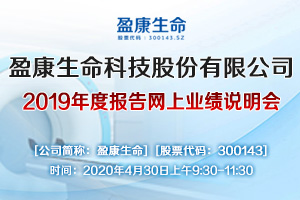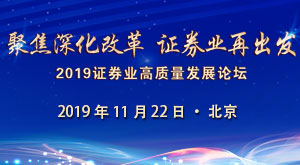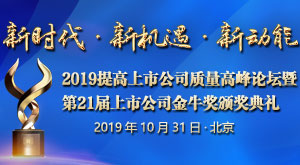歐元區改革難以一蹴而就
說清楚歐元區問題的根源以及研判未來歐元走勢,恐怕不得不從國際收支視角對歐元區的經濟模式進行思考。觀察一國經濟既有內部視角也有外部視角,外部視角往往是內部視角的鏡像。由于全球經濟波動反映為一國的外部風險,從反映一國外部風險的國際收支視角來觀察本國經濟運行癥結或許更能做到清晰明了。
總體而言,自歐元區成立以來,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國際收支結構普遍存在經常賬戶逆差擴大、金融賬戶順差擴大的特征。與國際收支結構變化同時發生的是,這些國家政府債務水平的持續上升。
在1999年歐元區形成之前,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經常項目處于盈余狀態,而德國則處在0-500億歐元的逆差區間。在歐元區形成之后,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經常項目則持續出現逆差;而德國恰恰相反,經常項目順差呈現加速態勢,從2000年的逆差400億歐元一直上升至2012年歐債危機時的2000億歐元順差。
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德國依靠其自身先進的制造業實力,越來越多地占有了歐元區既定的外需份額,這同時對應著區域內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外需份額的下降,致使其經常項目持續逆差。
對應到國民收入恒等式中,當一國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在私人儲蓄無法提高,也就是高福利政策導致的私人儲蓄率較低的情況下,必然對應的是公共儲蓄的下降。而公共儲蓄的下降即為該國財政赤字的提高,政府債務水平的上升,同時也可能伴隨該國銀行業債務水平的提高。
作為身處歐元區的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由于沒有獨立的貨幣自主權,無法將其財政赤字貨幣化,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債務和銀行債務風險最終顯性化。
同時,在金融項目上,由于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經常項目出現逆差,只能依靠金融項目的資金流入來彌補,又將導致這些國家的外債增加。一旦其國內債務持續高企到一定程度而無法維持,或者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比如美聯儲加息或者歐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政府債務風險或者銀行業風險就會暴露,從而會刺激資本外逃,引起外債風險暴露,形成經常項目和金融項目雙逆差的國際收支風險。
上述分析是從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來看歐元區的經濟風險,如果站在德國的角度來看,情況又如何?由于歷史上德國飽受通脹的困擾,因此其在財政紀律方面非常嚴格,對財政赤字非常謹慎和敏感。歐元區成立以來,德國的公共儲蓄水平不斷上升,財政赤字不斷下降。截至目前,其政府債務水平維持在65%。與公共儲蓄水平上升相對應的是經常項目持續盈余,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從2000年逆差1.7%上升至2012年歐債危機時盈余7.5%。
由于同是歐元區國家,德國的公共儲蓄水平上升,即財政赤字下降以及經常項目盈余的上升,要求其他歐元區國家也應該使本國的公共儲蓄水平上升,財政赤字下降。但由于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執行嚴格的財政紀律以降低財政赤字需要通過經常項目盈余、擴大外需來滿足,而既定的外需份額已更多地被德國占據,從而形成一個悖論。
綜上可以看出,雖然歐元區的問題表現為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國的財政債務危機或者銀行業債務危機,但實質上卻是其內部經濟模式所致,即經常項目分配不平衡的危機或者說在區域內各國外需分配不均衡。
當然,德國與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制造業實力差距懸殊導致國際收支失衡是一種市場選擇,但這種市場競爭的結果畢竟是在歐元區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歐元區成立這一制度變化確實帶來了區域內各國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
今年以來,隨著意大利政局動蕩、銀行壞賬問題顯現以及歐元區經濟的積弱難返,歐元區改革迫在眉睫。在2018年12月上旬的歐盟峰會中,歐盟各國財政就支持歐元區應對未來金融危機的措施達成一致意見,賦予歐元區銀行業聯盟更多金融實力和帶有主權紓困基金性質的歐洲穩定機制更大的靈活性,但由于法國和荷蘭、北歐國家存在分歧,并未在歐元區預算和共同安全儲蓄體系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這些后續問題將會在未來的歐盟峰會上進一步磋商。在此期間,由于意大利債務問題以及英國脫歐對歐元區經濟的影響等風險仍存,歐元區改革不會一蹴而就,一旦出現歐元區區域內的債務或者金融風險,以德國妥協為主的危機救助模式仍將是大概率事件。